
有一位日本禅师,日日修行,也没什么别的嗜好,唯独喜欢甜食。在他病重的时候,弟子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探望,当然也不忘带一些点心送给恩师,好让他在圆寂前尝一尝。到快要坐化的那一刻时,老禅师一如其他道行高深的修行者,端坐席上,神情平和。但然后,他竟然拿起了一块甜饼,放进口中,有点艰难地慢慢咀嚼。吃罢,他微微启唇,好像要说点什么,于是弟子们统统紧张地凑过去,心想师父要做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开示了,非得好好听清楚不可。老禅师终于说话了,他只说了两个字:“好吃!”然后就断了气。
一个人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想的竟然还是适才甜品的滋味,留下的遗言竟然还是对那块甜品的赞美,没有任何告别,更没有不舍与恐惧,他还不算最厉害的美食家吗?所谓的美食家难道不就该是这般模样吗?一心一意地对待眼前的食物,心无旁骛,甚至置生死于度外。
后来大家都说这位禅师真是高,已经达到觉悟的境界了,理由是佛学的修行最讲究一个人是否时刻“正念”。
“正念”指的就是非常专注地活在当下,走路时专心走路,睡觉时专心睡觉,不执着于过往发生的事,也不忧虑未来的烦恼。这种状态自然是快乐的,同时也是无我的,因为它完全切断了“我”的过去与未来,不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也不把将来的“我”看成是现在这个“我”的延续。要在平常达到这种状态已经很难,要在死的那一刹仍然保持这种状态就更难了,所以很多人都认定这位“甜品禅师”是真正的涅槃了。
其实我们天天进食,又何曾试过每一餐每一口都专心地吃呢?吃早餐的时候看报纸,吃午饭的时间变成一场工作会议,晚餐吃的是“电视汁捞饭”。我们有多久没试过好好地、一心一意地对待眼前的食物了?如果我们专心地吃,食物的味道会不会变得和平常不一样呢?我们常常为一些吃斋的人感到可惜,为一些饮食上有诸多禁忌的人扼腕。可是回头细想,我们平常囫囵吞枣地吃东西,甚至吃这一顿的同时就念着另一顿,难道这就是享受了人生、懂得饮食的乐趣了吗?
看来美食家起码可以分成两类:绝大多数都是心思敏捷,想象力丰富,吃一块肉的时候,会回味起从前远方某家菜馆的手艺是如何高明,或者惦念着明天的一顿盛宴;少数像甜品禅师这样的,则全神贯注于眼前所见、嘴中所尝。对这种人来讲,或许连一口白饭都是人间至味。
日本还有一位以烹调料理闻名的禅僧藤井宗哲,他曾经在新干线的一趟列车上遇见一位青年,这个年轻的上班族把公文包放在膝上当小桌,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杂志,顺便拿出便当来吃。
宗哲和尚注意到,这位青年“是以看杂志为主,顺便吃便当”。他的行为“不过是把‘进食’当作机能性动作,也就是将食物放入口中,机械地咀嚼后,经过喉咙,最后储存在胃袋”。宗哲和尚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位上班族,发现“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杂志,根本感觉不到便当的存在。这类人的饮食生活,可称之为‘机器人进食’”。
说来惭愧,我也是个进食机器人,常常一个人吃饭,吃的时候也是丢不开书本杂志,生怕浪费了吃饭的时间。再推想下去,平日的工作餐或饭局,岂不也是如此?为什么很多饭局明明叫了一桌子菜,走的时候都剩下许多未尽的菜肴,偏偏回到家后还会觉得饿呢?那是因为在饭局里我们往往专注于说话而忘了食物。没错,食物常常不是饭局的主角。我很少听到有人说:喂,有家餐厅很不错,我们约某某一起去吃吧。绝大部分的情况是反过来,先是想好要约哪些人,然后才去找个饭馆成全大家的聚会。
无论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看书报电视,还是一堆人找个吃饭的地方开会谈生意,都是我们不想浪费时间的表现。真是讽刺,这是个美食发达的年代,几乎人人都是美食家,偏偏我们还会觉得吃饭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大概人们心中有个标准,觉得日常三餐仅是必要的营生手续,可以随便打发,任意填上其他活动;而美食,则是一种很特别、很不日常的东西,必须严阵以待。
不过,要是我们用对待美食的态度去对待最简单不过的食物,又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前几年,越南高僧一行禅师来香港访问。在他主持的禅修营里,他教大家用很慢很慢的速度吃饭,吃的时候不要交谈,全神贯注于眼前的菜肴,这就是所谓的“正念饮食”了。一行禅师曾以“橘子禅”说明正念饮食的方法:不要像平常那样一边剥橘子一边吃,而要专心地剥开橘子的皮,感受它刹那间射出的汁液,闻它散发于空气中的清香。然后取出一瓣橘肉,放进口中缓慢地嚼,全神贯注地体验门牙咬断它、臼齿磨碎它、舌头搅动它等每一个动作,直到它几近液化,被吞咽下去为止。
如果你这么做,你会对一瓣最普通的橘子产生前所未有的全新感受。你还会发现自己用不着专程购买一枚昂贵的意大利血橘,因为你根本不曾知道什么叫作吃橘子。最美妙的是,这种修行还会引导你注意吃的过程,仿佛,你不曾吃过。
比一行禅师的橘子禅更夸张的,是美国佛学导师康菲尔德的葡萄干修行法,他教导学生们用十分钟去吃一颗葡萄干,很多人吃完之后竟然觉得太饱了!
我们不可能每一顿饭都这么吃,但至少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练习心无旁骛的正念饮食。你也不用觉得它是个宗教色彩很浓的仪式,你只需要把它当成认识美食的基本练习就行了。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道证法师
道证法师 蕅益大师
蕅益大师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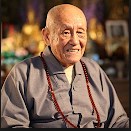 梦参老和尚
梦参老和尚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