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宋仁宗《修心偈》曰:“初祖安禅在少林,不传经教但传心。后人若悟真如理,密印由来妙理深。”(《嘉泰普灯录》卷十一)可谓深得“教外别传”的精髓。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楞伽经》卷四说:“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计着名字者,不见我真实。”愚人只看到指头,而看不到月亮。执着于语言文字的人,怎能看到真理的本身?《大慧语录》卷二十说:“古人云:‘见月休观指,归家罢问程。……归家到了,自然不问途程;见真月了,自然不看指头矣。”
这段话后半部分的内容,在禅宗语录中常有引证。意思是释迦牟尼佛从鹿野苑开始说禅,直到入灭的四十九年间(五十年是约说),虽然一生都在说禅,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说过。契嵩特别强调说,禅者所谓“教外别传”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没有在语言文字上说出来的这一部分内容。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说不立文字,是因为语言使存在发生了混乱,甚至有丧失存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因此,当我们感动于一幅美丽的图画时,我们就处在物我两忘的意境中。但当我说:“这真是一幅构图优美的图画”时,原来那完整的境界便已经断裂成为“我”和“那幅构图优美的图画”了。
语言文字不但会我们与存在疏离,而且还会引起歧义。有一个禅师写了两句话让弟子们参究,那两句话是:“雨两人行,天不淋一人。”弟子们得到这个题目后,便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两个人走在雨地里,有一个人不淋雨,那是因为他穿了雨衣。”有的说:“一定是有一个人走在屋檐底下。”有的说:“这两人,是一位母亲,肚子怀了一个孩子。所以只淋到一个人。“大家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个没完没了。最后,禅师看时机已到,就对大家揭开谜底:“你们都执着于‘不淋一人’的说法,而且执着得很厉害,争论不休,殊不知越争论,离真相就越远。大家想想看,明明说‘不淋一人’,不就是说两个人都在淋雨吗?”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禅宗化用成语守株待兔的典故说(《林间录》卷上):
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
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桩旧处寻。
诗的意思说,意义像一只活泼的兔子,苍鹰(喻有慧根之人)一见即将它活捉生擒。没有灵性之人,就好像那只知守株待兔的猎狗。这种人只知道在字面上兜圈子,殊不知当在这些语句上纠缠不休时,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早已消失殆尽了。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肇论·涅盘无名论》说:“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倡无说以显道,释梵绝听而雨华。斯皆理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
佛陀在摩竭陀国说法,众生不肯奉行,佛陀遂于石室中坐禅三月,不使一切人天入室(《诸佛集要经》上)。净名杜口,即维摩默然。《维摩经》中,三十二位菩萨各自解说什么是不二法门,后来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什么是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遂赞叹他真正得不二法门的三昧。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须菩提有一次在岩室中禅坐,帝释天称赞他善说般若,散花供养。须菩提说:“我并没有讲过什么,怎么说我善说般若?”帝释天说:“尊者无说,我亦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于是天旋地转,花雨飘落得更多。禅不可说,语言文字皆空,故释迦掩室,净名杜口。须菩提岩室坐禅,帝释天雨花赞叹。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就是指事物的本体,你能用语言表达的就不是“道”了。如果一定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那就要使用羚羊挂角式的语言。所谓羚羊挂角式的语言,就是禅师在说法时使用的玲珑剔透、不落痕迹的语言:禅师说:“我如果说东道西,你们就会寻言逐句。我如果羚羊挂角,你们还向什么地方摸索?”(《景德传灯录》卷十六)传说羚羊晚上睡觉时,将两只角挂在树上,足不着地,这样一来,纵是嗅觉灵敏的猎狗也找不着它的踪迹了。在禅宗看来,“羚羊挂角”的句子就是“活句”,即超出逻辑思维、意路不通、无意味的语句,而那些能够通过逻辑思维来理解的语句则是“死句”。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庄子》说:“今者吾丧我。”吾丧我,就是把小我提升为大我,把大我升华为无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摘自吴言生《参禅开智慧》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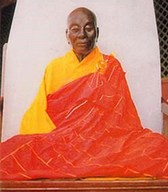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净慧法师
净慧法师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道证法师
道证法师 蕅益大师
蕅益大师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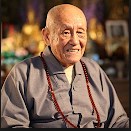 梦参老和尚
梦参老和尚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