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高僧印光大师(1861~1940)和谛闲大师(1858~1932),一位是中兴净宗的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一位是传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法嗣。两位大师佛法上互相探讨、修持上互相激励,在弘扬佛法和教化众生的事业中,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堪称最相契的莲友,为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结缘普陀山
清光绪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检阅料理,缺人帮助。当时印光大师住北京阜城门外圆广寺,众以师做事精慎,推荐师去查印刷事务。化闻和尚见师道行超卓,南归时,请师同行,安单于法雨寺藏经楼,为法雨常住首座,主理藏经。
清光绪二十四年,了余和尚时为普济监院,请谛闲法师讲《法华经》。谛公欲为其师作一养老处,乃曰:“我欲在此山修一茅蓬养静。”了余乃于旃檀庵后为之建筑,名曰“为莲蓬”(“慧莲蓬”)。次年,谛闲法师来住 “为莲蓬”。后欲请其师来,其师之友不肯,令远去,因此谛闲法师也不住了。印光大师闭关结束后也曾应请,到“为莲蓬”暂住了一段时间。两位大师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结缘相识。
二、志同道合
印光大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在阐扬教理方面,多依天台宗,先后精心校对刻印多部天台宗典籍,如《随自意三昧》、《法华入疏》等。谛闲大师教演天台,行归净土,对弘扬净土也是不遗余力。这就奠定了两位大师志同道合的基础。谛闲大师在《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序》中说:
“闲四十年来,奉释尊之诚言,遵智者之悲愿,所以自修而兼利者,其归结处,亦不外一句弥陀,信愿往生而已。今契西居士等,重将印公文镌板印行,以垂永远。手民将竣,问序于予。利人益物,共结法喜之缘;流水高山,一为知音之奏。”
三、佛法上互相探讨,修持上互相激励
大约在两期闭关之间的1900年,印光大师给第一期闭关的侍者融明法师去信,叮嘱他要亲近净业知识,“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同时提到:
“谛法师专修净业,予料其必得大利益。以彼撑持道场种种心,皆死尽无余,念佛之心,又恳切之极。恐彼深得三昧,我尚未能一心,他日何颜见彼?故当仁不让,又欲闭关。大约总在普陀,未知定归何所。”(《增广印光文钞卷一·与融明大师书》)
既对谛闲大师专修净业表示赞叹,又自我策励,欲再闭关。
1901年,印光大师在法雨寺闭关潜修,致信谛闲法师,谈念佛体会和对宝王随息念佛法门的看法,并问谛公的意见:
“光自出家以来,即信净土一法。但以业障所遮,二十年来,悠悠虚度。口虽念佛,心不染道。近蒙法师训励,誓期不负婆心。无奈昏散交攻,依旧昔时行履。因日阅十余纸净典,以发胜进之心。至宝王随息法门,试用此法,遂觉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涌澜翻。想久而久之,当必有雾散云消彻见天日之时。又查《文类》、《圣贤录》皆录此一段,因悟慈云十念,谓藉气束心,当本乎此。而《莲宗宝鉴》亦载此法。足见古人悬知末世机宜,非此莫入,而预设其法。然古人不多以此教人者,以人根尚利,一发肯心,自得一心。而今人若光之障重根钝者,恐毕生不能得一念不乱也。故述其己私,请益高明。当与不当,明以告我。光又谓只此一法,具摄五停心观。若能随息念佛,即摄数息、念佛二观。而摄心念佛,染心渐可断绝,瞋恚必不炽盛。昏散一去,智慧现前,而愚痴可破矣。又即势至都摄六根法门。愚谓今之悠忽念佛者,似不宜令依此法。恐彼因不记数,便成懈怠。有肯心者,若不依此法,决定难成三昧。法师乘愿利人,自虽不用,当为后学试之,以教来哲。若是利根,一七二七定得一心。纵光之昏钝鲁劣,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乱矣。”(《增广印光文钞卷一·与谛闲法师书》)
1921年,谛公63岁时,于夏历二月间,偶患风湿入里之症。印光大师闻讯,致信殷勤问候,并建议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信中说:
“二月下旬,闻公自温归来,身婴笃疾,手足不便运动。光固知我公悲心深重,欲令现在诸学子及一切四众,及早努力修行,勿待病魔临身时,则不易摆脱矣。其直以口说,尚恐不亲切,遂现身以说,可谓深慈大悲,无以复加矣。光自愧财法两缺,欲效愚忱,直无其力。但只旁问于根祺、然云辈。后闻佛曦谓病已复原,但足尚不能大行。意谓行固能行,但艰于出外而已。昨万年寺住持了悟见访,问及,言吃饭说话,与好人无异,唯手足绝不能动,虽饮食便利,一一须人代为周旋。光窃念病体如此,何以弘法?或令浅见之人,谓佛法无灵,以故数十年讲经,天下闻名之大法师,身婴痼疾,只管求医服药,亦不见愈。彼素谓依教修持,能转定业,及阿伽陀药,万病总持者,皆诳人耳。若其不诳,彼当依教转彼定业。彼素崇净土,以弥陀名号为阿伽陀药,何不服之?又《普门品》、《观音圆通》,讲时不晓得多有道理,直是菩萨跟到称名求救者。彼既如此,何不放下身心,拌一条穷性命,志心念观音菩萨,以求身心悉皆安隐以及得大解脱,获真圆通也?光念世人多有此见,倘我公能仰求大士垂慈,即令贵体复原,福慧崇朗,则彼浅知浅见者,将断尽狐疑,增长正信,当相率而出邪途,入佛道,以期普利自他于无既也。是诚所谓以大慈悲,现身说法也。其利益大矣!”
谛闲大师的回信充满真挚的感情,非常感人。信中说:
“印公鉴:读手示,不禁神驰泪堕。闲早知夙业深重,到六十三时,必难过此一关也。是以前年在京时,都中诸巨子与闲再订来京之约,闲曰:‘且过六十三后,方可再订来期耳。’不意于二月十六夜,忽内蕴大蒸,一昼夜间,顿觉两手麻木,两脚沉坠。自此以后,举动即不便矣。闲尔时便知是果报之病,非药饵所能治也。想是多生所作三途业因,其宿种熟时,必直招三恶道报,决无疑贰。所幸诸佛深慈,菩萨悲念,念闲此生为僧三十余年,以全副精神实心宏法,或将重报轻偿,犹未知也。荷蒙慈悲,垂示持念大士圣号,敢不唯命是从?然闲于起病后,虽诸缘未曾尽情放下,而西归之志决矣。常念四大无常,身为苦本,倘能早一日往生,便是早一日离苦得乐时也。而每日独静时,唯佛是念,亦唯佛是归。时想从今以往,既唯佛是归,决定可免三恶道果。如是思惟,心生欢喜。殊不知将经百日,不但未见往生影响,而诸病亦渐平复,即手足亦见转重为轻。自料二十日后,只恐依然步履如常矣。足证娑婆之苦缘不易脱,而极乐之净因不易成也。闲何人斯?大法关系,本所不计。唯冀我公,调摄精神,为法自重,时赐教言,以匡不逮,是所至盼。肃复并候佛安。”
两位大师的通信,充满了互相关怀和以佛法为重的精神。印光大师所期望于谛公的,谛公已自觉地身体力行,不久就彻底痊愈,继续讲经,的确足以祛浅信者疑惑,为法门之光荣。大师给卓智立居士的信中说:
“佛不救人人自救,汝此言出于疑心。汝若真悟此理,则念大士念佛,虽大士与佛止之,不可得也。虽是众生自度,非仗大士与佛为增上缘,则不能也。(知此理,纵令谛闲法师病不愈,亦不疑大士有所不及。而谛师是年七月即讲经,汝未之闻乎?)”(《印光文钞三编卷二·复卓智立居士书四》)
1932年夏历七月,谛公往生。七月上旬,方圣照居士给印光大师来信报告谛公往生情形,大师回信表示:
“谛公之逝,的确往生。其去之景象,尚不至惊天动地者,以讲说时多,专用净功时少也。在常人如此,则颇不易得,在谛公则犹未能副其身份。谛公既去,座下法将如林。其知命之法子,光皆不能望其项背。函中谓佛教二大砥柱,已折其一,其一以光当之,则不知光但一吃粥吃饭之庸僧耳。承谛公不以无状见弃,相交三十多年。然光于人事应酬,概不举行,只朝暮课诵回向一七,以尽我心而已。”印光大师不以人情为准,而以法益为准,对最相契的莲友的往生,与对后学弟子的往生一样,唯以念佛的真实利益来回向。
四、弘法上互相支持
主要体现在共同劝赞流通契理契机的经书,共同保护庙产、护法卫教上。
光绪三十年,谛公为温州头陀寺请藏经,请印光大师一起去北京帮助料理一切。经已印完,尚须几日方行,印光大师到琉璃厂各书店看看。一店中有两部《拣魔辨异录》,大师通请来,以一部送谛公,冀彼流通,一部自存。
民国七年(1918年),叶恭绰、蒯若木、徐蔚如等居士请谛公到北京讲《圆觉经》,期间白城隍、关圣帝君和周将军(周仓)等相继临坛与谛公谈论佛法,徐蔚如居士把这事记成一本《显感利冥录》行世。观宗寺书记僧根祺师给印光大师来信并寄来《显感利冥录》。印光大师看后送给其他法师看,看到这本书的人大多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印光大师于是在给根祺师的回信中开示:“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这样揭示白、关用心处,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
继民国十一年农历四月初八上海功德林蔬食处创办之后,谛闲法师、开如、了余等法师与道尹黄涵之等乡绅,创办宁波功德林蔬食处,提倡戒杀吃素,印光大师为撰《宁波功德林蔬食处开办广告》。
民国十四年 (1925年),大约夏历五月,谛闲大师弟子方远凡居士排印谛公讲演的《慈悲道场忏法随闻录》,请印光大师作序。大师序中介绍该忏法的缘起,指出梁武帝未知净土,所以后之礼忏者,悉当注意于回向往生,方获究竟实益。又阐述修行之要,敬为第一。
民国十五年 (1926年),印光大师为谛闲大师讲演《大云》编辑骆季和居士钞记的《始终心要解略钞》作序,并对该书详细校对,订正错讹。
奉化孙玉仙居士拟另刻《护法录》板,祈谛师作序。谛师以日与学徒讲演台教,不暇命笔。孙居士遂托谛师请印光大师撰《重刻明宋文宪公护法录序》。序言阐述弥陀辗转现身之大慈悲心。
民国十八年 (1929年)夏,谛公弘戒哈尔滨,归过大连,潘对凫、施省之等居士请其讲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恐南北语言不通,因先出讲义,印500本。潘对凫居士给印光大师寄一本并请大师作序。序中略叙观音之本迹及此经流通注释之来历。
民国十九年,印光大师为谛公所著的《念佛三昧宝王论疏》作序,阐述佛所开的净土特别法门的大义:“令以深信切愿,专念阿弥陀佛圣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则由三昧宝证实相宝,方知此宝遍满法界,复以此宝普施一切。”
某年,闻内务部将应薛京兆尹之请,颁布寺产登记条例。谛公和印光大师联名致书段执政,分析其议与民国十年颁布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相抵触,不合法不合理,要求饬部将是项建议取消,以免苛扰佛教。
五、共同教诫皈依弟子
民国七年,徐蔚如居士将印光大师《文钞》20余篇印作一本,陪其母来普陀求皈依,大师令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十七年徐居士来函言:“前欲皈依,师令皈依谛公,十年以来,心中终觉不慰,仍祈许以皈依。”大师回信说:“汝决欲皈依,即此便可,至于法名,仍用谛公法名,又何必另取乎?”类似徐蔚如居士这样既皈依谛闲大师,又皈依印光大师的居士不在少数。而两位大师各自的皈依弟子,也往往同时向两位大师求教学习,两位大师也共同教诫在家出家后学。
例如印光大师在《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中开示:
“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懂),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谛闲大师皈依弟子方圣照居士和方子梵(远凡、志梵)居士母子,印光大师给他们的开示信件达15封之多。
印光大师皈依弟子温光熹虽得大师剀切教诲,仍以带病之身历经北京、南京、普陀、宁波、上海拜访高僧大德。拜访谛闲大师时,大师嘱咐他不要忽视净土法门:“志愿生西,是为正判。车不横推,理须直断。”(《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二十七期载有谛闲法师 《送温光熹居士返川序》)
谛闲大师的弟子显荫法师从日本留学回国,染病后去上海修养,印光大师去信提出殷切的期望和告诫:
“唯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但现在年纪尚轻,急宜韬晦力修。待其涵养功深,出而宏法,则其利溥矣。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无涵养,或所行所言有于己于法不相应而不自知者。此光区区愚诚也。了道师已来,勿念。春风易于入人,祈保重调摄,当勿药有喜矣。”(《印光文钞三编卷一·复显荫法师书》)
谛闲大师皈依弟子顾显微居士劝友人潘承锷念佛,彼致书反难,谓不能生信,更为滋疑。顾以其书寄印光大师,令辟驳之。大师将书寄去,谓宜勿投。顾即致书云:
“弟言不能生兄之信,断兄之疑,因求某法师为书,其书已寄来,但其语言毫无谦逊,直言无隐,不避忌讳,恐致冲突,故不敢寄。”
彼云:“我病深,非狼虎药不能治,愈不忌讳愈好,飞寄。”
顾即寄去,其心佩服,皈依谛闲法师,而畏印光大师之直口,绝不一通音问。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道证法师
道证法师 蕅益大师
蕅益大师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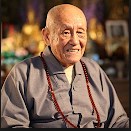 梦参老和尚
梦参老和尚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