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来东土,到汉地传法的多是外国僧人,人们按照中土习惯,并为方便称呼,往往要给他们起个简化的音译汉姓。开始的时候,人们多用这些外来僧人本国或地区名称中的字作姓,如翻译《四十二章经》的竺法兰、竺摄摩腾,翻译《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的竺佛朔,东晋时与道安法师共同研究禅观的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来自天竺,所以“竺”为姓;安世高,本是安息国太子,后出家学道,所以就以“安”为姓;曾在东吴大阐佛法的康僧会来自康居;汉末号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支谶、支亮、支谦三师徒,以及支敏度等,都是来自大月支;又有帛尸梨蜜多法师,“帛”字是西域某国名的略称。这是较为早期的外来僧人取姓方法。
到了后来,人们对佛教的认识逐渐深入,开始以“佛、法、僧”三字取为僧人的姓氏。如在南北朝时以传习上座部禅定著称的佛驮跋陀,翻译《华严经》的佛度跋陀罗,翻译《四分律》的佛陀耶舍,还有“现种种神异以弘大法”的佛图澄等,都是以“佛”取为姓氏的;“法”的梵语是“Dharma”,音译为“昙摩”或“昙无”,以此取为姓氏的有三国时期到洛阳专弘律藏的昙摩流支,为汉地律学始祖的昙摩迦罗,南朝宋时来建康译经的昙摩密多,翻译出《中阿含》、《增一阿含》的昙摩难提,晋武帝时期赴西域求法的昙无竭,北凉时期著名的翻译大师,《优婆塞戒经》的译者昙无谶等,都是以“法”取姓的;以“僧”为姓的则有南朝宋时担任戒师的僧伽跋摩,南朝梁时在杨都译经的僧伽婆罗,北朝秦时与道安法师共译《阿毗昙毗婆沙》的僧伽跋澄,以及同时代译出《阿毗昙论》、《阿含经》的僧伽提婆等,都是取“僧伽”为姓氏。
《避暑录话》曾云,“佛法始来汉土,僧犹称俗姓,或称竺,或弟子多呼师之姓。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故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蜜多,故为帛。”这里指出的是汉地出家人取姓氏的情况,大多跟从师父的姓氏,如支遁拜支谦为师,出家后就姓“支”。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先经过四五百年的民间潜伏期,到南北朝时由佛图澄在北方开创一崭新局面,佛教僧团取得合法地位,汉地出家人数骤增。到了澄公弟子道安法师时,开始注意僧团组织的建设工作。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发现原来出家人的姓氏太过混乱,不适宜佛教的统一和发展,就倡言:“佛以释迦为氏,今为佛子者,宜从佛之氏,即姓释。”开始大家都有些茫然,等到《增一阿含经》传译过来,其二十一品有云:“四大河入海,亦无本名字,但名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于如来所剃除须发,三法衣,出家学道,无复本性,但言沙门释迦弟子。……是故诸比丘,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迦弟子。”天下僧人乃信服而从之。《易居录》卷22云:“沙门自魏晋已来,依师为姓。道安尊释迦,乃以释为氏。后见《阿含经》云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沙门,皆称释种。自是遂为定式。为沙门称释之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僧人统一姓氏通称为“释”,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文化意义。在中国,“姓氏”是标志一个家族的符号,天下僧人通称“释”,就表明大家都是同一信仰的一家人,这就大大增强了佛教内部的团结与组织的统一。另外,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长、流布、发展,必须经过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天下僧人统一姓氏为“释”,可以视为佛教与中国人民生活相契合的开始,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从此,佛教对中国的社会生活逐渐有了重大影响,例如仅仅在名字方面,魏晋以来,“号取寺名,诏用佛语,人以僧名,几若无事可以离佛”。古代以“僧”命名的人也不少,较为著名的如王僧达、王僧虔等,初生婴儿,父母恐其多病多灾,往往要取个僧名作为乳名,或寄养佛寺,或穿僧人衣物,或拜僧人为师,以期佛菩萨加被,消灾免难,健康成长,例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小时候就曾经寄养于尼寺,拜智仙为师,取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13岁时才回家。直到近代,中国仍有类似的习俗,“小孩不清吉者,多投寺记名,以和尚道人呼之。”可见这种影响的深远。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 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妙莲老和尚
妙莲老和尚 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 其他法师
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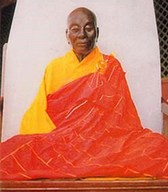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净慧法师
净慧法师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