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正月廿一是净土宗第九代祖师蕅益大师圆寂日。蕅益大师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国土板荡、风雨飘摇的时代。但即使处在这样的环境,佛教界也出现了如莲池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这样的中兴领袖,其中,蕅益大师一生为法忘躯、精勤不已,且贯通儒释、著作宏富,终成为名满天下的净土宗祖师。
然而,少年时的大师却是反对佛教的,那么,他是如何尽弃前非,最后又归心净土的呢?这是一个极其传奇又曲折的故事。
以千古道脉为己任
据《年谱》(弘一大师撰)记载,蕅益大师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俗姓钟,名际明,又名声,字素华,又字振之。晚号“蕅益老人”,别号“八不道人”。江苏吴县木渎镇钟氏子。父名岐仲,持诵大悲咒十年,母亲金氏梦到观世音菩萨抱着一个小男孩送给她,生下了后来名闻遐迩的大师。
当时的父母已经四十岁了,年龄老大,加上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孩子,自然宠爱有加。因生在佛化家庭,大师很早就开始诵经礼佛,七岁吃素,而且持斋非常严格,曾经梦到观世音菩萨相召劝勉。
到了十二岁,父母送他出外就学。这时候的大师读了很多儒书,虔心于格物致知之要、居敬慎独之功,张扬得意,以传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不仅作了数十篇雄赳赳、气昂昂的论文批驳佛教,而且从小茹素、久断荤腥的他这时开始喝酒吃肉了。此举真令父母大跌眼镜!要是换做今天,恐怕父母早就气急败坏地四处追着打了。
倾心佛教,淹贯诸宗
然而,蕅益大师的父母毕竟是讲道理的。母亲严厉的教诲,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阅读了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序》和《竹窗随笔》,才幡然悔悟,从此不再谤佛,并将以前所有辟佛的文稿付之一炬。
二十岁时,诠释《论语》“颜渊问仁章”中孔子回答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对“天下归仁”之语起发疑情,随即苦参力究,不能下笔,废寝忘食三昼夜,大悟孔颜心学。
然而此时,父亲不幸亡故,大师为父亲诵《地藏经》超拔,由此萌生出家之心。
后听一法师讲《楞严经》中 “世界在空。空生大觉” 时,怀疑为何有此大觉,能为空界做出预先安排,闷绝不知所措。此时决意出家,体究生死大事。
天启二年,在一月中三次梦见憨山大师,痛哭缘分浅薄、相见太晚。本欲从憨师出家,然而千里迢遥,遂依憨山大师的高足雪岭禅师出家,命名智旭。
出家后的大师如鱼得水,饱餐佛法甘露,于宗门教下,深参力究。第二年夏,坐禅于余杭径山,体究功极,身心世界忽皆消殒。因知此身从无始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但是坚固妄想所现之影,念念刹那不住,的确非父母所生。自此,性相二宗,一齐透彻;一切经论,禅宗公案,无不现前。随即觉悟到此境界非为圣证,故绝不语一人。久之,则胸次空空如也。这个境界,即是天台“六即”中的“名字位”。
二十八岁那年,母亲病重,大师回家亲自侍奉汤药,并四次割身肉做药引,冀望以此孝心令母亲增福延寿。然而,母亲最终仍然病亡。料理完丧事后,即往深山闭关,以参禅功夫求生净土。
大师看到当时戒律衰颓,为匡正戒律,阅律三遍。虽然对于戒律的解悟很深,但自愧烦恼习气强烈,行持不够,故终其一生从未与人授戒。
三十二岁时,大师私淑天台,究心台部。以天台教观匡救禅宗之弊,尤志求五比丘如法住世,令正法重兴。
矢志安养,一意西驰
永历二年,大师已经五十岁了。某天他对成时法师说:“我从前念念想要恢复比丘戒法,近年来却念念想着求生西方了。”成时法师听了非常惊讶。后来才知道,大师在家时发大菩提愿,后来为匡救圣教,终生孜孜力行。
径山大悟后,彻见近世禅者之病,在绝无正知见,非在多知见,在不尊重波罗提木叉,非在著戒相。故抹倒禅之一字,力以戒教匡救。尤志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令正法重兴。后决不可得。遂一意西驰,冀乘本愿轮,仗诸佛力,再来与拔。至于随时著述,竭力讲演,皆聊与有缘下圆顿种,非法界众生一时成佛,直下相应,太平无事之初志矣。
由此思路一转,大师晚年就专修净业了。在《自像赞》中,大师自况:“不参禅,不学教,一句弥陀真心要。不谈玄,不说妙,数珠一串真风调。” 念佛矢志净土的目标确定,又假之以忏悔自讼,洗濯心垢,藉此惭愧种子,方堪送想乐邦。大师以身说法,感人至深。
大师的文字般若皆从彻底悲心中流出,可谓婆心切切。故日本京都沙门光廉比丘在1723年重刊《灵峰宗论》序中说:“余亦尝言,读蕅益《宗论》而不堕血泪者,其人必无菩提心。”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敬仰赞叹蕅祖“言言见谛,语语超宗,如走盘珠,利益无尽”。又赞言“宗乘教义两融通,所悟与佛无异同。惑业未断犹坯器,经雨则化弃前功。由此力修念佛行,决欲现生出樊笼。苦口切劝学道者,生西方可继大雄。”
印光大师又曰:“若论逗机最妙之书,当以《净土十要》为冠。而《弥陀要解》一书。为蕅益最精最妙之注。自佛说此经以来之注,当推第一。即令古佛再出于世,现广长舌相,重注此经,当亦不能超出其上。”此言可谓高山仰止,心心相应之语。
永历八年,大师示疾,当时他寄给钱牧斋的信说:“今夏两番大病垂死。季秋阅藏方竟。仲冬一病更甚。七昼夜不能坐卧。不能饮食。不可疗治。无术分解。唯痛哭称佛菩萨名字。求生净土而已。具缚凡夫损己利人。人未必利。己之受害如此。平日实唯在心性上用力。尚不得力。况仅从文字上用力者哉。出生死。成菩提。殊非易事。非丈室谁知此实语也。”
大师病到七日七夜不能合眼,唯有痛哭称念佛名,专求佛力救拔,这对自负高慢者,不啻当头一棒。
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正月二十一日午时,大师趺坐绳床,向西举手而寂,世寿五十有七岁,法腊三十四。僧夏从癸亥腊月至癸酉自恣日,又从乙酉春至乙未正月,共计夏十有九。
流水有心终汇海。纵观祖师一生含辛茹苦,护持圣教,为报四重恩,树立禅、教、律、密、净之正法,匡正儒家宋明理学之弊端,救世之慈心、宏愿、深忍、大行。最后导归净土,藉乘本愿轮,再来救度娑婆苦难众生。其深慈大悲,贯彻始终,令见闻者无不兴起,被后世奉为净土宗第九代祖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 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 妙莲老和尚
妙莲老和尚 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 其他法师
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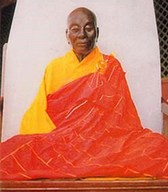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净慧法师
净慧法师 绍云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