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俗家四老中,有两位是因肺癌去世的,前后仅相差两年,却因有无三宝的加持及阿弥陀佛的慈光照摄而境遇迥然不同。
名医的尴尬
我的岳父是一位离休老干部,生前还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他解放前参加革命并入了党,解放初期即担任区委书记,后又考上了昆明医学院。因其生性耿直,在校期间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的滇东北小县,一呆就是将近四十年,直到去世。在边远的小县医院里,一个医科大学生自然是难得的人才了,岳父内科、外科、儿科乃至妇产科门门精通。几十年来,因其德技双馨,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由衷钦佩与信任。在那个年代,提起某医生的大名,可谓老幼皆知。他晚年当选为县政协常委,直到八十年代离休。
一九九四年,岳父肺部出现不适症状,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他心里有不祥的预感。经成都华西医大附院拍片检查,确诊为肺癌,他决定回家采取保守疗法。
第二年,岳父的病情加剧,最终病卧在床。那时岳母和笔者本人虽然都已学佛,且已皈依数年,但对于如何运用佛法实在是茫然无知,更不用说运用阿弥陀佛慈悲救度的净土法门,实则和未学佛者没有两样,面对家中危病的亲人束手无策。笔者更是舍本逐末,一心扑在气功上,想以此为亲人做些什么。
说起气功,在八九十年代,可是如潮流般席卷中国。笔者当时也是弄潮儿,不仅积极投入修炼,还热情广学弘传,与同道创设了气功协会并担任理事长,开班授课,“讲经说道”,县级几大班子领导也积极参与,政府还一度拨出气功事业专项经费。因此,在岳父病倒后,我就坚持“发功”为其调理,但依旧未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临终前夕,肺癌的剧烈疼痛也不因为是名医而有丝毫情面可讲,亲人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注射吗啡止痛无效后,笔者至诚恳切发功为其止痛起了一些有限的作用。每当其疼得实在无法忍受又无法入睡,只要有机会,笔者都会在床前运动真气发功,只希望老人能少受些折磨。笔者自幼失怙,婚后岳父一直待我如亲出,故对岳父有深挚之情。
每次发功时,心里真诚发愿:只要能减轻亲人痛苦,我宁愿减自己的阳寿。每次发功后,会暂时显效,老人慢慢平静下来而入睡。但随着病情加剧,其平静入睡的时间越来越短,由最初的个把小时,到半小时,到片刻,终于再真诚的发愿和拼命的布气也无济于事了。五月初,岳父在痛苦中离去,时年六十九岁。
当时县里没有一个出家师父,惭愧末学在当地被信众喊作“老师”,可糊涂的“老师”连如何给自己的亲人助念都不知道。现在想来真是深深汗颜。
小学老师的幸运
母亲生于书香门第,解放前即念完了高中,解放后参加工作,终生担任小学教师,几十年下来可谓桃李满天下。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她除了眼睛高度近视外,一生无甚病痛,晚年患白内障,经手术治疗也没啥大碍。退休后直到七十六岁以前,身体相当不错,偶尔伤风感冒,也不去医院,自己去街上药房买些中药冲剂之类的就完事。
二〇〇六年下半年,她有些咳嗽,开始以为是普通感冒,也没当回事,只弄些药吃吃。可这次却始终不见好,终于进医院检查。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看过拍片后认为不太妙,建议到大医院做个全面检查。结果出来后果然不出所料,已经是肺癌中晚期,失去手术治疗价值。医生朋友劝放弃手术,莫让老人冤枉受苦。
令人奇怪的是,从检查的各项指标及癌细胞扩散度看,通常情况下此时的患者应该会有明显的疼痛,可母亲唯一的不适就是咳嗽程度逐渐加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异样。
在未离开老家前,大约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份左右,笔者就已与金山寺的师父联系,希望能让母亲皈依三宝。但此事颇有难度。因笔者向来与母亲难以沟通,一切说服工作由几个学佛的女居士朋友(也是母亲最信赖的)来操作。先是陪着她去寺院玩耍,吃吃斋饭,慢慢说些学佛上的事。当家师是笔者的好友,也积极进行引导,终于在其七十六岁生日前皈依了三宝。有一段时间,母亲天天晚饭后由几个女居士陪着去寺院打坐念佛,一坐将近一个小时,令大家感到惊异。
在肺癌确诊后,鉴于岳父的景况,笔者此时一心想的是依靠三宝的加持,绝对不让母亲有同样的痛苦,遂天天持念大悲咒回向母亲。
在把母亲送到三哥处后,我决定正式出家,以此出家功德回向母亲。二〇〇七年四月,笔者如愿以偿地在浙江某寺剃度出家,而此时的母亲也住进了医院接受保守治疗。六月,母亲病情加剧,咳嗽更明显,呼吸越来越急迫,以致于需要靠输氧维持了,但依旧没有痛感。
据三哥朋友讲,那时她的肺部几乎全溃烂了,但病人不觉得痛的事实让大家难以理解。因此,我们一直未把实情告知母亲,对她说是肺炎,是严重肺炎,因几十年来未得什么病,所以这次一病起来就特别严重。所以,母亲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癌。
在住院期间,我们请了母亲在老家时最亲近的一位女居士去照料,其一有空闲就诵《佛说阿弥陀经》给她听,在这个单人病房中整天用念佛机播放“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儿子那年正好高考,最后一科考完就匆匆赶过去,每天下午在病床前给奶奶诵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可以说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都一直浸润在佛法慈光里。只因没告知实情,无法引导往生的话题,只有女居士在与其闲聊中侧面说一些而已。
平时白天一切由女居士照料,晚上三哥换班。六月二十四日晚,母亲临睡前却让三哥去隔壁睡,让女居士来陪护床睡。据女居士讲,那晚她大约是十一点半左右入睡的,由于白天疲劳了,一入睡就直到天亮。大约在七点多醒来时,发现母亲已经安然往生了,具体是夜里何时断气的完全不知。
笔者赶到时,人已送殡仪馆装入冰棺,母亲面容很安详,略带些微笑,好多人都以为是化了妆,三哥说并未化妆。
俗妻与老家几个居士一起赶过来参加助念。平时她每天要礼佛两百拜,因连夜赶火车不便礼拜,所以赶到后就在冰棺前一百次礼拜回向。在一百多拜后,她看到母亲坐了起来,似乎是跃出了冰棺顶上,双腿盘坐着,伸出右手轻轻往下一按,好像是说连夜坐火车,你也辛苦了,不消再拜了,这景象维持了几秒钟。出殡的头天晚上守大夜,有一居士闻到了异香,那绝对不是房间里殡仪馆提供的那种香味,是她以前未闻过的。
第二天,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并没有即刻把遗体送往火葬场,因远在美国的二哥要在七天后才能赶到,所以得把遗体在冰库里存放七天。笔者那时虽已出家,比几年前料理岳父时进步多了,却依旧不太明白助念送往生之事,也未召集大家助念,直到告别仪式结束,工作人员要往冰库送了才想起助念。于是叫住工作人员,请求稍等一会。
五六个人围在冰棺两旁开始持念阿弥陀佛名号,站在旁边的五妹和对面的俗妻开始哭了,一边念佛号一边哭;几分钟后,对面的俗妻一下转哭为笑了,也就是同时,笔者听到了突然扩大了的念佛声,不是几个人的声音了,好像有好几十人,是从上空传下来的。声音浑厚,十分悦耳,好像那种混响的音箱效果,一直和着我们几个人的声音。因想到人家工作人员在等着入冰库,所以也未久念,很快终止了助念,我们的声音一结束,上边的声音也消失了。
工作人员在忙的时候,我们几个就忍不住一起说开了,原来个个都听到了上边和进来的念佛声,俗妻更是激动地说就在声音扩大的同时,她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从空中下来,然后母亲从冰棺中升起,随着菩萨一并去了。观音的形象就是原来家里客厅供的那个模样。
在返回住地的中巴车上,大家还余兴未消,又说起空中念佛声之事。这时三哥及老家过来参加助念的两个亲友(他们未信佛)也饶有兴趣地插话了。原来我们在里间助念时,他们几个或蹲或站,在外边房子里聊天、吃烟,也是听到了突然扩大的念佛声,当时也没在意,还以为是这样的仪轨,即先小声念,后大声念,听我们一议论,方知不是仪轨的要求,扩大的声音是来自上空。
以上种种不可思议之瑞相,说明母亲往生确定无疑。比较十二年前的岳父,真是天渊悬隔啊!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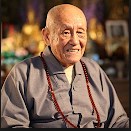 梦参老和尚
梦参老和尚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 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妙莲老和尚
妙莲老和尚 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