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清修院的时候,正是一个早晨。到了门口一叩门,里边出来一个小和尚。他的名字叫宗祥,看样子长得很聪明,很如法(听说他后来已竟还俗),他问我:“你来有什么事?”
我说:“来拜见清池和尚。”
于是,他领我进去,与清池和尚相见。我们见面之后,谈了些过去的事情,清池和尚又问我:
“你这一次来做什么?”
“我来要出家!”
清池和尚一笑,接着就说:“你上次想出家未成,这一次胡思乱想地又要出家?”
清池和尚的意思,以为我大半不知又为了一点什么事,自己起烦恼忽然一阵想出家,过不了三天半就又松劲了。但他待我很殷勤,吃、喝、住、睡都方便。晚间我们谈起话来,他还是劝我不要出家,他说:
“你家里还有许多人,不要胡思乱想,轻易就要出家!你在我这里可以多住几天,住够了再回家,免得家里孩子大人惦念!因为,我见过很多人都是一时想出家,出家之后又想家,悔不该出家。就这样出家又回家的,不知有多少?”
“我与他们不一样!”我忽地抢过来说,“我已经研究佛经多年,在家里,生活虽然不很好;但有那一座小药铺,还能够维持的不错。尤其是当医生的,在社会职业方面来说,也得算上流。所以按生活方面来说,我出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衣、食、住,也不是为逃避现实;我的目的,是因为自己研究佛经已经有七、八年的工夫,仍然不知佛法的宗旨落在何处,自己想出家受戒之后,到各地去访明师,好好参学参学。将来有机会可以宏扬佛法,使佛经流通世界,人人皆知!不然,世风日下,人欲横流,没有一点挽救的办法。同时,在过去我年青的时候,也学过一些外道,后来又学医卜星相;自从看过佛经之后,觉得学佛法,比那些医卜九流各行道,要高上多少万倍也不止!所以我出家,是自己从心所愿,并不是为环境所迫,也不是有什么背景。”
经过我这么一说,他知道我出家心业已决定,再也不可遏止,于是他说:“好!你既具有决心,愿意发心出家,就满你的愿吧!”
当时我预备拜清池和尚为师,他说:
“我小庙容不了你这位大神仙!拿研究佛经来说,我不见得比你研究的深。你如决定要出家,我可以给你作介绍。现在南方有月霞、谛闲二位老法师;北方有静修(时任北京潭柘寺东寮)、印魁(时已圆寂)二位老和尚。这四位大德之中,有一位已经圆寂,其他三人具在,而且都是道高德重,与我很要好。你现在出家,无论想拜谁为师,我都可以给你介绍。”
“你不要会错了我的意思!”我说,“我认了师父之后,并不想仰仗师父的培养,希望师父给我留下多少房产,做多少衣服,出家之后,住在小庙里衣暖食足地去享受、去安闲,我决不是这种意思!我的希望,只是能在师父跟前出家挂一个号,受戒之后,随我的便到各地去参方。享富也罢,受苦也罢,一切都用不着师父来分心!将来我的机缘成熟时,可以到各地宏扬佛法,机缘不成熟,我也可以用功修行!”
“好啦!”清池和尚说,“你可以随意在这几位大德中认一位作师父吧!”
话虽这样说,究竟我也不知应当认哪位师父好,总是犹豫未决,后来清池和尚让我在佛前拈阄。于是我在佛前烧上香,磕了头,把四位法师的名字拈好,结果拈着了已竟圆寂的印魁老和尚的名字。当时清池和尚说:
“这次机会很好,这也是该当你与印老有缘。他过去在南京任毗卢寺方丈九年,在方丈任内圆寂,为人很耿介,很修行,对于个人的操守行持,非常谨严!平生不收徒弟,所以他死后也没有人接续。我也常以此事为憾!准备后来有适当人选的时候,给他代收一个弟子,以了我的心愿。现在你预备到这里来出家,拈阄的时候又拈着了印老的名字,恐怕这也是感应!你心里愿不愿意?不愿意的话,我再给你介绍那三位现在的师父。”
我的意思是只要有位师父挂上号,能够得到出家就可以,哪管他望空拜师,不望空拜师呢!所以当时就顺口承认了拈得的阄。清池和尚还说:
“印魁老人在南京已经圆寂了,他现在还有一位师弟叫纯魁,刻下住涞水县瓦宅村高明寺,你现在出家,他还可以替师兄代收。”
出家的事,算得着他的允许了,只等到涞水县高明寺去落发。不过在去落发之前,依然在清修院住着。清池和尚因为我过去是居士,有些话不好意思当面直接说;现在既然要决心出家,而又什么也不懂,那么对于新出家的这些个理路,就不得不痛快地告诉一下了。
“你知道吧!”他训诫似的对我说,“你在家的时候,是当医生,虽然不是富贵人家,可是人人见了,都要恭敬你。出入的,都是车接车送,与社会一般人比较起来,得算很有身份。可是出家则不然,就是八十岁新出家,也得算一个小和尚;师父坐着,徒弟得站着;师父吃,徒弟得在一边看着,不知出了家你能不能这样虚心?”
“还有一层,就是你刚出了家,虽然是四十多岁,还得算一个小沙弥。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了受戒的比丘,不论其年岁大小,一律要称师父。两个人在路上走对头,当沙弥的,必须站在路旁,让比丘走过去,然后当沙弥的再走。初次见面,不论其年纪比自己大小,都要向他行跪拜礼。如果来了挂单的,须先接过担子或包袱来,送到他屋子里,然后,先打洗脸水,后打洗脚水,种种的都伺候完了之后,再恭恭敬敬地给顶一个礼。大众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要比别人先吃完。走路的时候,要在紧后边走。早晚要打鼓,撞钟,下板,收拾佛堂,打扫院子……这些事都是沙弥应办的。你酌量酌量,能受得了这些苦?干的来吗?”
“好!”我慨然都答应了。
本来,这些都不算一回事。例如在家人,为了经商坐贾,为了争名夺利,还得起早睡晚,低三下四。我们是出家人,想了生脱死,办这出世的事情,起早睡晚就更算不得一回事了。俗语不是说吗?“做买卖如修行。”这话是说做买卖的人,什么样的苦到时候也要受,什么不耐烦的事情到时候也要耐烦!不然,你的买卖就做不好。那么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修行人如做买卖。”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什么吃苦耐劳的事,也要做!无论什么不能忍耐的事,到时候也要虚心下气地去忍耐。久而久之,自然把自己的性子磨练得很驯伏了。
这虽然是很平常的一点事,可是如果能够在平常时,永远维持着这个恒心,使它一直地平常下去,这就很不平常了。因为出家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巧法,也不是什么希奇古怪,是人人能办,人人能成,无论念佛也罢,参禅也罢,从智门入手也罢,从行门入手也罢,只要你能永远去实行,就绝对能成功。所以当时我对清池和尚告诉我的话乍然一听,似乎是不很习惯,其实,到了做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平常得很!
在清修院住过几天,清池和尚就领我到涞水县高明寺去落发。那时正是三月天,天气不很冷。从天津坐火车到高碑店换车,正赶那一次没有车,清池和尚说:“我们不坐火车,要步行,看看你能不能吃这苦。”从高碑店到涞水县的瓦宅村,还有很远的路程,我们到高明寺的时候,已竟是半夜。叫开门之后,我那位纯魁师叔首先就问:
“到这时候赶来,有什么要紧事?”
“因为印和尚一向也没收个徒弟,”清池和尚走的气喘喘地说,“现在有一位发心出家的,拈阄的时候,正是拈着印和尚的名字,这是他们有缘,今天我送他来落发。”
纯魁师叔,一听说为师兄收徒弟,心里很欢喜,就准备与我落发。高明寺的宗派是临济正宗,到我这一辈是“隆”字。纯魁师叔对于给师兄收徒弟的事很重视,还给我看看八字,五行中缺金,就配了个“衔”字,所以我出家的法名是“隆衔”。
落发之后,他们两个人还开示我一番:
“出了家如同又降生一次,像另转成一个人一样。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从此改头换面,做丈夫事,行人之所难行,做人之所难做。将来主持佛法,宏范三界,成无上觉,为天人师,方不负出家学道一场!‘隆衔’两个字,如同刚一下生起的乳名,受戒的时候,再按照名字的意思,起一个学字。出家之后,最初要先学戒,由戒生定,因定发慧,这是最要紧的事!”
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深深地画了一道鸿沟,至此,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在一个简短的仪式里换上了出家的衣服,先拜祖,后拜诸山,两天的工夫,把我出家的事办完,第三天回清修院。从此我步入了佛门。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 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妙莲老和尚
妙莲老和尚 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 其他法师
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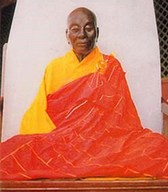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净慧法师
净慧法师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