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八年之秋,是我人生所走过的五十六个春秋中经历悲欢离合的一段日子。
十月十一日,我参加了乐至县报国寺第二期念佛七,在那里,身心得到净化。
十月十九日,公公去世,丈夫是六零后独生子女,丧事全靠我们夫妻二人承担,累得半死。
十月二十四日,忙完公公丧事,我组织放生回来,得知体检结果:左下脑有3cm×2.1cm的肿瘤。
十月二十九日,我住进医院。
十一月二日,进行开颅手术,切除肿瘤。
我不知别人得知自己重病后是什么心情,如何处理,我只知我的第一念就是求生极乐,立刻放生。当时,放下万缘,生死交由阿弥陀佛安排,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凑钱,将钱寄出,请成都的师兄帮我放生,也许此次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放生了。
何去何从?找谁医治?丈夫六神无主。我跪在三宝前发愿:生死交由阿弥陀佛安排,我的任务只是念佛。住院前,我对九十岁的老父亲以及我的丈夫交代,我有两个底线:第一,若我术后成了植物人,请别医治,我不想浪费医疗资源;第二,若我昏迷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别让我吃肉。
住院后就开始接受检查,第一件事是要将一头青丝剃光,我以为我会很不舍,不料,剃后,我很喜欢我的光头。
十一月二日上午七点四十,我被推进手术室。此时,我真的像是待宰的羔羊,什么都靠不住,唯有通身依靠阿弥陀佛,将医护人员想成是佛菩萨派来的使者,要么就是接我回极乐,要么就是让我立刻康复。
两个多小时里,我被推到手术室后,在一个角落里等待着。此时,我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我早先对丈夫和女儿说:“你们与其在外焦急地等待,不如在外为我念佛。”此时,全家人也齐心协力,一心念佛。虽说平常我每天念佛三万,但与此刻比来,仍属泛泛悠悠。我念到醒来时,手术已经结束,时间在十二点五十九分。
我术后的情况,让医护人员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是三宝加持的力量,只是不学佛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一是我在手术室里时就立马清醒。很多人术后被推进病房好久了,都还没完全清醒。
二是术后一个多小时就吃了一个苹果,晚上就吃稀饭,第二天吃了手抓饼和豆浆。大部分人第三天才进食。三是我第三天就下床走动了。而我邻床病人与我同病,大我十一个月,术后一直昏迷不醒,待她稍醒,我劝她念佛,在她临终时,我一直为她通宵念佛号。
为我主刀的医生第三天查房时,对我丈夫说了两句话:“她现在的情况,在国外(即以国外的出院标准)可以出院了。学佛就是好。”
没想到此次住院,我像一束阳光,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清洁大爷爱到我病床前做清洁,我婉拒,他说:“一看你就是一个好人,我站在这里,安心。”护工对我说:“你是我这么多年来,见到的第一个这么开心、阳光的病人。”护士说:“你是我们科室最勇敢、最能作表率的病人。”医生说:“见你第一眼,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当时我们还没给你做手术,心里就认为你不会有事的,果然不负众望。”
我是神经外科手术最成功,术后恢复最好、最快,没有一点后遗症的病人。
我将病房当作闭关房(去年到庐山东林寺闭关后一直念念不忘),凡邻床病友进手术室前,我都劝她们念佛,我也为之念佛。为静心念佛,我婉拒了百分之九十的亲朋好友到病房探望,还有百分之十的亲人不顾反对而来到病房。每天,因受病痛折磨,同病房的人通宵叫痛,我将身心放空,放在阿弥陀佛处,头痛它的,我不去管,只管每天念佛不少于六万声。
但对于术后的饮食问题,我与医生以及我的家人发生了分歧。医生和家人要求我吃肉、蛋、牛奶,伤口才好得快,但我已吃长素十三年,不可能为肉身而损害我的慧命。最后达成一致协议:不吃肉,可适当吃蛋和牛奶(忏悔)。
此次生病至今,我觉得好像生病的人是我而非我。说是我呢,毕竟有受(昏、痛);说非我呢,我从不认为我在生病,好像生病的人不是我,毕竟,我从没将它当回事,全身心在阿弥陀佛上。
相反,我非常感恩这次病苦。生病前,虽说这十多年来,我每天完成三万声佛号,但心从未空闲过。每天除了工作,还有做不完的家务,以及对家中四个老人操不完的心。这两年更是有受不完的气,老人老了,就老小老小了,我也深知是老人给我送福报来了。另外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人与事。
这次一查到重病,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终于可以放下了,终于可以休息了,终于可以“刑满释放”(回极乐老家)了。心情是如此的美好,每天,我放下万缘,认为这世上的任何人与事都与我无关了,除了吃喝与输液,我就念佛,每天念佛不少于十二个小时,天天开心、无烦无恼,难怪别人认为我与众不同。
这次生病,师父们为我开示,师兄们为我念佛、放生、回向,亲朋好友们为我送来关爱和祝福,家人为我衣不解带,更有师兄发愿愿舍自己的寿命延长我的寿命。阿弥陀佛啊,我有何德何能,受如此大福?只能精进修行,回报大众。
南无阿弥陀佛!
《净土》2019年第2期 文/妙音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 道证法师
道证法师 蕅益大师
蕅益大师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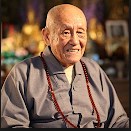 梦参老和尚
梦参老和尚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