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老房子。一层楼贯通的走廊尽头,阳光斜洒一地,祖父母正祥和地打着“二七十”(一种四川乐山一带才有的长条纸牌),看见我,祖父抬起头,如常般说,“回来了?”趋近,他们忽然消失不见。椅子上,只有两个叠放的骨灰盒。——猛然惊醒,四周漆黑一片。眼角有热的东西滚出,是泪。明日就是祖母的三七了。
2015年12月8日,父亲打来电话,很平常的语气,但我还是敏锐地察觉出一丝紧张。他说,“你祖母今天住院了,咳嗽,可能是肺炎。”上次回家,给祖母切脉,右寸浮数,底下无根。心里知道不太好,但脉学学得浮皮潦草,只是找藏族朋友购买了一些虫草,嘱她每日服用。一听父亲说祖母住院,顿生心疑,立即定了次日9号的机票。到晚上,父亲果然又打来电话,说CT照出两肺有大量阴影,疑似肺癌。“不去确诊吗?”“确诊的话,要去成都的大医院,还要做手术切下一小块肺做活检,你奶奶年纪大,我和你叔叔商量了一下,怕她经不起折腾,就不去了。”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跟领导请假,一边密密地打电话给熟悉的僧人、认识的寺院嘱托药师佛和长寿佛法事。领导们也极好,立即商量出一个不需要我在西藏做的选题,让我可以安心回家数月,兼职工作。9号到重庆(比飞成都便宜几百元),在师弟家住一夜,第二天中午便搭乘高铁回了四川老家。
作为佛教徒,我想了很多自己该做的:法事、供僧、放生……肺癌是一种不能被治愈的绝症,我所求的,不过是让祖母能尽可能多活一段时间。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打破了。
在医院陪护几天后,她不愿输冰冷的液体,非要回家。父辈跟医生沟通,对方也同意在家休养——“等死”这个残忍的词,在每一个人心里盘旋着,每个人却都紧闭了嘴,不肯将它吐露出来。回到家,祖母的病情开始平静地恶化。在医院时,她白天好歹能靠在调高的病床上,坐着看电视或聊聊天。回到家,坐着便觉憋闷、喘不过气,只能侧躺。问了医生朋友,说是肿瘤持续扩大,压迫了气管。祖母平时爱看中央三台,卧室的电视机就总是开着,歌舞的声音听起来热闹,也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我在她的卧室牵了网线,一方面是每日工作还得完成,一方面也是监护。写着写着,回过头看一眼,她总是沉默地侧卧着,瘦小的身形在被子底下一动不动。“奶奶”,我担心,唤一声,心里暗自怕她默默地去了。一开始,她总能应声。后来要叫几次,她才“嗯”一下。
病情,家里是瞒着她的,可我总怀疑,老人对这种事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她一定是察觉到了我们格外的殷勤和小心翼翼,她一定知道,这个病,绝不是我们宣称的普通的肺炎。可是她什么也不说,她只是沉默地侧躺着,不出声,也不随意叫我们。我不知道,是她所受的大家族教养让她选择将一切病苦咽下,还是担心“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一普适的世间规律,最终也将我们感染,不耐和嫌弃她。我面对着这老苦和病苦,不知所措。
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这老苦和病苦。祖父母经常锻炼,退休后每天都去老年活动中心打门球——一种从英国传来的球类运动,跟高尔夫有点接近,但比高尔夫不讲究场地,也舒缓得多。锻炼了二十多年,俩老都显得精神健硕。祖父去世时85岁,早晨还好好的,去打了球,买了菜,回来做了饭,下午打了麻将,晚上吃饭后突然感觉不适,急救车送到医院后,不到一小时走了。医生说,祖父是突发心衰。他临终时清醒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环绕身旁的儿孙说,谢谢你们都能来看我。这样的年龄,死前又没受什么罪,几乎是“喜丧”了。可是祖母不一样。从病发到死亡,我目睹了整个过程。在盲试印度的肺癌药“易瑞沙”时,她的身体出现不良反应,脸部浮肿,眼皮都近乎透明;她的皮肤耷拉下来,松松的,发着黄;她早晨五点不到就醒来,只是睁着眼,等天明;她的胃口也变差了,用小米熬的粥,加点胡萝卜和香油、盐,也只能吃浅浅的一小碗。
她是爱整洁的,可是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对我和姑姑说,她要用纸尿布。我从超市买了纸尿裤回来,跟姑姑合力帮她换上了。过了几天才知道,她躺着根本尿不出来,必须下床,坐在净桶上,才能尿出来。“那干脆今晚还是不要套纸尿裤了,反正你也要下床”,姑姑说。
“不”,她努力地说出一整句话,“我提不起裤子。”我鼻子猛然一酸,强忍着没让泪流下来。我不知道她已孱弱至此,连如厕后拉上裤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在死亡那强有力的阴影面前,所有的干涉都显得幼稚而可笑。
她的血氧含量不断下跌,从离了氧的86%,跌到输氧时的70%。这很危险,是会随时窒息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生命一点一滴流逝,仿佛看得见似的,从她的躯壳里往外散。我不忍心让她拖着衰弱的病躯苟延残喘,不再祈祷让她寿命延长,而是死前少受病苦。倘若能换一个崭新而健康的身躯,在理智上讲,其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只是,我所受过的所有关于老、病、死的教诫,第一次鲜活起来,仿佛刺一样地扎着自己的心。我恍然意识到自己从前所有关于老、病、死的设想,都是浅薄的自以为。世间诸苦的巨流啊,我只是初初地尝到了一斛,便已觉惊心动魄。
1月13日清晨,祖母殁了。
全家人急匆匆地都赶了来。急救车也到了,测了心电图,说“已经走了”。父亲嘶哑着迸出哭声,一向理性的叔叔也好几次哽咽。我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能哭。中阴身如果因儿孙哭泣而心生眷恋不忍,是会影响往生的。我坐到遗体枕边,喃喃念诵着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这是一段最为漆黑最为漫长的路,而我们,都没有办法和您一起走过。我把您托付给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也请您相信他们,追随他们吧。
六岁那年,祖父母将年幼的我接到身边抚养。一带,就到我考上大学。而我现在能做的,所有的念诵、祈请、磕头、放生、供养,面对他们的恩德,都是那么微不足道。父亲和叔叔安排好了后事。当天停灵去陵园,第二天火化,第三天下葬。我想起自己在拉萨参加的葬礼。停灵七日,期间二十四小时延请四人以上僧团轮班念诵。停灵房间外,数排酥油灯持续不灭。猫狗等动物,要暂时寄存到别家去。那一家,只是民族习惯性地信佛,但传统仍延续着。而在汉地,传统随着快节奏的生活,渐渐也湮灭了。想起已圆寂的先师曾讲过,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所做的善业,对祖先会有利益。于是决定了,祖母七七之中,尽可能多做大乘长净戒——守持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饮酒、不佩戴香鬘严饰、不往视歌舞伎乐、不坐高广大这八条戒律,并素食及过午不食,为期一日一夜的别解脱律仪。
三日后,下葬了。
坟地是现成的,昔日为祖父购买时便预备了双穴。主事人是个道士——不是真道士,原只是个算命的,后来发现死人的生意好做,又轻松又赚钱,遂去成都混了个道教皈依证,回乡后一本正经地穿个道袍,挥舞个桃木剑,俨然就是个道人了。他很懂民间那一套,也知道如何化解亲属残余的悲痛。一套套滑稽的词儿从他嘴里冒出,伴随着抛洒五谷,“保佑子女升官发大财,保佑做官做到中 南海……”亲属们哄堂大笑起来,道士念一句,大家就高声吼一句“好”!丧事也有了喜事的气氛。仿佛封了墓穴,祖母便摆脱了生前的病苦,以一个轻盈而健康的身躯跟祖父久别重逢,大家时不时还可和附近的“老鬼”们一起打打麻将、玩玩纸牌。我在一旁,只感觉一种隔膜的荒谬。倘若死是这么令人欢乐放松的事情,我们又何须为亲人的逝世悲恸,何须畏惧死亡?……可是人们从不追问,只是理所当然地看待生老病死……葬礼完成,大家踩着一地的泥泞渐次离开。而属于我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在拉萨的时候,我每天用于修行的时间——广义的修行,包括听闻和思考、念诵和转绕——不少于四小时。现在是每天六到八小时,至少在这四十九天内,要加倍行持。另一些东西悄然变化着。
依然是拜三十五佛,依然是念诵经咒,依然是闻思佛法,依然去放生……但有些东西悄然变化着。
没有什么比死亡的冲击更大。如果有,那就加上老、病。必须更努力了……不仅为自己,也为将来有一天,面对更多亲人的离去。
一转眼,大半个月过去了。今天清晨,我梦见了祖父母,不由自主地流了泪。看看时间,五点左右。大概是祖母提醒我,该起床洗漱,洒扫供佛,在佛前自受大乘长净戒了。
这一生如果能持续精进,摒除恶行,最终发起正真的出离心与菩提心,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与最深的祭奠了。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 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妙莲老和尚
妙莲老和尚 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 其他法师
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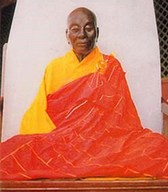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