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弘老来时,是在旧历的四月十一那天,北方天气——尤其是青岛,热得较晚,一般人,还都穿夹衣服。临来那天,我领僧俗二众到大港码头去迎接。他的性格我早已听说,见面后,很简单说几句话,并没叙寒暄。来到庙里,大众师搭衣持具给接驾,他也很客气的还礼,连说不敢当。
随他来的人有三位——传贯、仁开、圆拙——还有派去请他的梦参法师,一共五个人。别人都带好些东西,条包、箱子、网篮、在客堂门口摆一大堆。弘老只带一破麻袋包,上面用麻绳扎着口,里面一件破海青,破裤褂,两双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一把破雨伞,上面缠好些铁条,看样子已用很多年了。另外一个小四方竹提盒,里面有些破报纸,还有几本关于律学的书。听说有少许盘费钱,学生给存着。
在他未来以前,湛山寺特意在藏经楼东侧盖起来五间房请他住,来到之后,以五间房较偏僻,由他跟来的学生住,弘老则住法师宿舍东间——现在方丈室——因为这里靠讲堂近,比较敞亮一点。
因他持戒,也没给另备好菜饭,头一次给弄四个菜送寮房里,一点没动;第二次又预备次一点的,还是没动;第三次预备两个菜,还是不吃;末了盛去一碗大众菜,他问端饭的人,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吃,不是他还是不吃,因此庙里也无法厚待他,只好满愿!
平素我给他讲话时很少,有事时到他寮房说几句话赶紧出来。因他气力不很好,谈话费劲,说多也打闲岔。
愈是权贵人物,他愈不见,平常学生去见,谁去谁见,你给他磕一个头,他照样也给你磕一个头。在院子里两下走对头的时候,他很快的躲开,避免和人见面谈话。每天要出山门,经后山,到前海沿,站在水边的礁石上了望,碧绿的海水,激起雪白的浪花,倒很有意思。这种地方,轻易没人去,情景显得很孤寂。好静的人;会艺术的人,大概都喜欢找这种地方闲呆着。
屋子都是他自己收拾,不另外找人伺候。窗子、地板、都弄得很干净。小时候他在天津的一位同学,在青岛市政府做事,听说他到湛山寺来,特意来看他。据他这位同学说:在小时候他的脾气就很怪僻,有名的李怪——其实并不是怪,而是他的行动不同于流俗——因他轻易不接见人,有见的必传报一声,他同学欲与见面时,先由学生告诉他,一说不错,有这么一位旧同学,乃与之接见。
有董子明居士,蓬莱人,原先跟吴佩孚当顾问,以后不作事,由天津徐蔚如居士介绍来青岛,在湛山寺当教员,学识很渊博。他和弘老很相契,常在一块谈话,那时我每天下午在湛山寺讲法华经,弘老来听,以后他和董子明说:“倓虚法师,我初次和他见面时,看他像一个老庄稼人一样,见面后他很健谈的,讲起经来很有骨格!发挥一种理时,说得很透辟!”这话后来由董居士告诉我,我知他轻易不对人加评论,这是他间接从闲话中道出。可是我听到这话很惭愧,以后无论在何处讲经,更加细心。
朱子桥将军,多少年来羡慕弘老的德望,只是没见过面。正赶他有事到青岛,让我介绍欲拜见弘老,一说弘老很乐意。大概他平素也知道朱将军之为人,对办慈善及对三宝事很热心,乃与之接见,并没多谈话;同时还有要见他的人,他不见,让人回答,说已竟睡觉了。
有一天,沈市长在湛山寺请朱将军吃饭,朱将军说:“可请弘老一块来,列一知单,让他坐首席,我作配客。”沈市长很同意,把知单写好,让我去给弘老说,我到他寮房里一说,弘老笑笑没言语,我很知他的脾气,没敢再往下勉强。第二天临入席时,又派监院师去请他,带回一个条来上写四句话:“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思维,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朱将军看到这个条喜的不得了,说这是清高。沈市长脸上却显得很不乐意,按地方官来说,他是一个主人,又加是在一个欢迎贵宾的场合里,当然于面子上有点下不来台。我和朱将军看到这里,赶紧拿话来遮盖,朱将军平素有些天真气派,嘻嘻哈哈,把这个涩羞场面给遮掩过去了。
弘老到湛山不几天,大众就要求讲开示,以后又给学生研究戒律。讲开示的题目,我还记得是“律己,”主要的是让学律的人先要律己,不要拿戒律去律人,天天只见人家不对,不见自己不对,这是绝对错误的。又说平常“息谤”之法,在于“无辩”。越辩谤越深,倒不如不辩为好。譬如一张白纸,忽然染上一滴墨水,如果不去动它,它不会再往四周溅污的,假若立时想要他干净,马上去揩拭,结果污染一大片。末了他对于律己一再叮咛,让大家特别慎重!
他平素持戒的工夫,就是以律己为要。口里不臧否人物,不说人是非长短。就是他的学生,一天到晚在他跟前,做错了事他也不说。如果有犯戒做错;或不对他心思的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律己”不吃饭。不吃饭并不是存心给人呕气,而是在替那做错的人忏悔,恨自己的德性不能去感化他。他的学生;和跟他常在一块的人,知道他的脾气,每逢在他不吃饭时,就知道有做错的事或说错的话,赶紧想法改正。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几时等你把错改正过来之后,他才吃饭,末了你的错处,让你自己去说,他一句也不开口。平素他和人常说:戒律是拿来“律己的!”不是“律人的!”有些人不以戒律“律己”而去“律人,”这就失去戒律的意义了。
给学生上课时,首讲随机羯磨,另外研究各种规矩法子。随机羯磨是唐道宣律师删订的,文字很古老,他自己有编的“别录”作辅助,按笔记去研究,并不很难。上课不坐讲堂正位,都是在讲堂一旁,另外设一个桌子,这大概是他自谦,觉得自己不堪为人作讲师。头一次上课,据他说,事前预备了整整七个小时,虽然已竟专门研究戒律二十几年,在给人讲课时,还是这么细心,可见他对戒律是如何的慎重!因他气力不好,讲课时只讲半个钟头,像唱戏道白一样,一句废词没有。余下的时间,都是写笔记,只要把笔记抄下来,扼要的地方说一说,这一堂课就全接受了。随机羯磨头十几堂课,是他自己讲的,以后因气力不佳,由他的学生仁开代座,有讲不通的地方去问他,另外他给写笔记。随机羯磨讲完,又接讲四分律。
差不多有半年工夫,弘老在湛山,写成一部随机羯磨别录,四分律含注戒本别录,另外还有些散文。
他这次到北方来,也该当与北方人有缘,平常接受行律的,有很多学生,整个庙宇接受的还没有。虽然他在南方很多年,也没有能接受的,有也是部分的,暂时的,慈老法师在湛山时也说,南北到任何地方也没完全接受讲律行律的,原因是在末法时代,持戒是一件难事,不要说持戒,就是讲戒也是枯燥无味。为了自己不能行持,谁也不肯去发心;尤其是经忏门头,一个丛林里,住很多人,分子不一,谁也作不得主,如果马上让他去持戒过午不食,这简直太难了!
慈老和弘老到北方来,在别处,没有能拿整个丛林来接受其律仪的,惟湛山寺能接受。每到初一十五诵戒羯磨。四月十五,结夏安居,七月十五自恣,平常过午不食……二位老法师走后,这些年来,还是照规矩去行。原因这里是新创的地方,做事单纯,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复杂,自己也能作得主,也乐意,所以能接受。同时还有几位同学,继续弘老的意志,发心专门研究戒律,日中一食,按律行持;不但湛山寺是这样,和湛山寺有关系的庙如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天津大悲院……等也都按照这样去行。虽然不能完全做得到,但对戒律方面,能持几条算几条,持总比不持强。最低限度,出家人对四根本戒、十戒、十三僧残、应拣要紧的去行持。
例如半月诵戒,像演电影一样,诵一遍就等于在人的脑幕上映一遍,纵然不能完全持佛的清净戒,但起码也给人种一个持戒的影子,自己有污染的地方,也能在诵戒时忏悔,洗刷一下。拿持午来说,虽然有些人持的不如法,但不能为一两个人不如法,就把这条戒废弃不持。有这条戒,像一堵栏马墙一样,总比没有好的多。佛祖给后人立规矩大有意义,平常衣暖食足的人,欲心重,无明大,好睡觉,好做梦,这些都是修行的障碍!无明大的好惹事,几百人住在一起常闹事,事情就不好维持了。
弘老虽是生在北方,可是他在南方住的时候多,对于南方气候、生活、都很习惯。初到湛山时,身上穿的很单薄,常住给做几件衣服,他一件也没穿,向来不喜欢穿棉衣服,愿意在南方过冬。原因北方天气冷,穿一身棉衣服,很笨重的。
湛山寺本来预备留他久住的,过冬的衣服也都给预备了,可是他的身体,不适于北方的严寒,平素洒脱惯了,不愿穿一身挺沉的棉衣服,像个棉花包一样。因此到了九月十五以后,到我寮房去告假,要回南方过冬。我知他的脾气,向来不徇人情,要走谁也挽留不住,当时在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纸条,给我定了五个条件。第一:不许预备盘川钱;第二:不许准斋饯行;第三;不许派人去送;第四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第五: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这些条件我都答应了。
在临走的前几天,给同学每人写一幅“以戒为师”的小中堂,作为纪念。另外还有好些求他写字的,词句都是华严经集句;或藕益大师警训,大概写了也有几百份。末了又给大家讲最后一次开示,反复劝人念佛。临走时给我告别说:“老法师!我这次走后,今生不能再来了,将来我们大家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吧!”说话声音很小,很真挚,很沉静的!让人听到都很感动的。当时我点头微笑,默然予契。
临出山门,四众弟子在山门口里边搭衣持具预备给他送驾,他很庄重很和霭的在人丛里走过去,回过头来又对大家说:“今天打扰诸位很对不起,也没什么好供献,有两句话给大家,作为临别赠言吧!”随手在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纸条,上写:“乘此时机,最好念佛!”
弘一律师走后,我到他寮房去看,屋子里东西安置得很次序,里外都打扫特别干净!桌上一个铜香炉,烧三枝名贵长香,空气静穆,我在那徘徊良久,响往着古今的大德,嗅着余留的馨香。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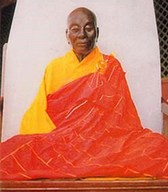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净慧法师
净慧法师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道证法师
道证法师 蕅益大师
蕅益大师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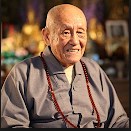 梦参老和尚
梦参老和尚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