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光生性不喜华靡,素以俭朴自守。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住在城郊西北一个小巷中,居所极为简陋,仅能挡风遮雨。夏天为避暑热,他请工匠挖地丈余,用砖砌成地下室,读书写作其间。大臣王拱辰当时亦居洛阳,所建宅第凌天高耸,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邵康节则打趣说:“一人巢居,一人穴处!
司马光不收任何人送给他的礼,就连皇上的赏赐也不受。仁宗皇帝临终前立下遗诏,赐予司马光等大臣一笔价值百余万的金珠。司马光考虑到国家财力不逮,便领衔上书请免。力辞再三未果,只好将自己那份珠宝交谏院充作公费,金钱接济了亲友,自家分文未留。司马光为官40年,仅有薄田三顷,所得薪俸大多周济了穷人。其妻去世时,竟拿不出钱来办丧事,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司马光临终床箦萧然,唯枕间有《役书》一卷,故吕公著为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
司马光府上有个仆人,30年来一直称呼他“秀才”。前来拜会的苏轼,听后觉得不恭,就教他以后改称“大参相公”。作为称呼,“相公”是指“位居宰相之职并享有公爵爵位的人”。司马光听仆人突然改口,吃惊地问他谁教的,仆人如实禀告。司马光说:“好好一个仆人,被苏东坡教坏了。”在司马光看来,“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他不仅自己不吝身份,也不希望家人为世俗所染,变得势利起来。
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在封建社会里,因势焰熏灼使然,官宦府邸中人,即便车夫、门子,身价也非同一般。如果家规不严、门风不正,他们就会倚权仗势,寻衅滋事,有恃无恐,横行不法,甚至贪污受贿,作奸犯科。据《清仁宗睿皇帝实录》记载,和珅的大管家刘全,查抄资产竟至20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即便在今天,领导“身边人”犯罪的案件也时有耳闻,这在司马光家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一天,司马光经过独乐园,见新盖了一间厕屋,就问守园者,建房的钱是从哪里得来的。守园者答,是我把游人给的赏钱积攒起来的。司马光说,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守园者说,难道只有相公您不要钱?守园者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句反问,就把主仆双方的为人都说清楚了。赏钱属于个人正当得利,留为己用合情合理,守园者却用于公共设施,这显然超越了一般职业操守。也许是我们对那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行径看得太多了,愈发觉得这位守园者可敬。他能这样做,无疑是受到司马光的熏陶。人格的魅力有多大,影响力就有多大。
在司马光手下当差,无势可仗,无光可沾,也无油水可捞,显然要比其他公府豪门清苦。但因主人夫妇待之以诚,持之以礼,从不欺凌打骂,他们活得自在有尊严,心里感到踏实,这可不是金钱能够买得来的。他们不仅安贫若素,没有怨言,而且也像主人一样平和敦厚,不慕奢华,不图富贵,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行胜于言,温公家风的形成,很大程度源自身教。“修齐治平”四字,司马光践履得十分到位。他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并视为“大贤之深谋远虑”。因此在身教同时,非常重视言教。《训俭示康》一文,就是司马光专门教诲继子司马康的。
由于身教言教并重,其家族后人也都以贤德立身,绝无“官二代”之累。司马光一生著述颇丰,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6种457卷。影响力大的除《资治通鉴》外,就是《家范》了。《家范》广泛收集了治家有方的实例,系统阐述了家庭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处世之道,为历代推崇的家教范本。司马光自己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因为家风是世风之基。



















 来果老和尚
来果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绍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道证法师
道证法师 蕅益大师
蕅益大师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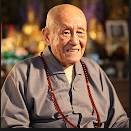 梦参老和尚
梦参老和尚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