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未来如果有人提起「圣严师父」,希望他们如何记得您们?
圣严法师(以下称师):希望别人怎么记得我?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对于历史人物,所能够留下的记忆非常有限,况且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历史人物,都还是个问题。
虽然有人抬举我,说我是历史性人物,未来一定能在历史上留名。但是,即使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也不一定能为后人所记忆,而且将来的人怎么看我、怎么记得我,可能有多种分歧的观点,即使是现在,大众对我的看法,一百个人也可能有一百种看法。
再说,未来也要盖棺才能论定,现在讲这些都是多余。人死之后,还去在乎后人是不是记得自己,根本毫无意义,也不重要。
问:要如何真实的活在当下?
师:在时间上,是有过去,也有未来,但是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这不是很空虚吗?但是如果只讲现在,而否定过去或未来,这也是错的。
以个人来讲,从父母生我们的那一刻开始到今天,就是我们的「过去」;对宇宙而言,它的开始,科学家提出是因为宇宙大爆炸而形成的,但是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依据科学家的论点来理解,然而这些都有过去的。
过去的事,现在已经捉摸不到。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讲,譬如我的出生地,现在是在长江底,淹没在水中,看不到了。我七十来岁时,曾回大陆去看我童年成长的地方,那里的建筑、河道、树木、地形、地貌都变了,人也不认识了,如果有照片的话,过去只能在照片里看到,或是只能存在记忆中了。
而未来还没有来,只能够想象,但是想象并不等于现实。譬如我们到访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前,可能已经开始在脑海里想象那个地方的人、物和建筑,等实际到达以后,才发现想象与现实是有差距的。
因此,过去、未来都是虚幻的,活在当下、把握当下最重要。当下是什么?譬如我现在是个和尚,做一日和尚就要撞一日钟,我的责任是什么?职务是什么?工作是什么?所处的环境如何?位于哪一个时间点上?都不能跟这些脱节。我要把握我现在的生命、现在的环境,负责任、尽义务,也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把握当下。这样的话,我是非常积极的,不会空虚,不会落空,也不会失望。
人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梦想未来,结果未来跟梦境不一样,所以失望。活在当下,就是做未来的梦。活在现在是最快乐的,如果放弃现在,老是回忆过去或幻想未来,那现在就会落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桩事。
疾病与信仰
问:就佛家的因果观念来说,请教您会如何看待这次的病情?您又是如何转念来接受这样的结果?您有没有沮丧过呢?
师:从单纯的因果观来看生病,是非常消极的,好象是我过去做了什么坏事,现在要受生病的果报。虽然这种解释法不能说错,但也不尽然正确。
譬如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上度众生,但是他的一生之中,经历很多的苦难;又如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取经,一路历经八十余难,难道这是因果业报吗?是因为他过去做了坏事,所以这一世要遭受苦难的果报?
另外,我们也看到历史上许多高僧,都是从艰苦之中走出来的。有位古德曾说:「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这就是说,对佛教的修行人而言,不论是发愿成佛或者成为一名高僧,都必须经过苦难的试炼,许多例子皆是如此。
刚过世不久(2005年)的印顺法师,他十多岁起即患了结核病,他的一生都是在吃药打针中度过,跟医药结了不解之缘。但是也因为经常害病,体力孱弱,因此专志投入于佛经和学问的研究,最后在佛学上有相当高的成就。
我的一生虽然比不上他们,却因为生长在战争不断的时代和环境中,所以我的一生也都是苦难。我一出生就不健康,到了五、六岁还不会讲话,在八、九岁之后才开始读书。我虽然没有读过中学和大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最后到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这段期间,我的健康情况仍旧不佳。
不论是到日本或是到美国,我都是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赤手空拳的努力。当时佛教界并没有栽培人才的概念,因为本身没有人,也没有力量。而我见到佛教如此衰微,只有鞭策自己更努力,同时我也发愿,我自己未能读大学,但是将来我要办大学,使得所有的出家人都有学位。
以这个过程而言,是因为过去我做了坏事,所以要惩罚我吗?不是的。反而我很感恩这一生有此际遇、有此一生,感恩佛菩萨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让我有机会奉献。
我三十多岁时已经写了很多书,这几十年来,即使再忙、再累,每年还是会写几本书,所以到现在我已经写了一百多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果吗?其实是佛菩萨给我的使命,也是我自己从小发的愿心。
我从小就有一个愿心,我想「佛法这么好,是误解的人却这么多!知道的人这么少。」因此我要竭尽所能把我所知道的佛法的好处、佛法的智能传播、分享给全世界的人。可是我的所知、所能非常有限,所以必须充实自己、加强自己,让自己具有传播佛法、分享佛法的能力。就像刚才枢机主教所讲的,点亮一支小蜡烛,能够照亮空间,让自己走路无碍,也让在空间里的其它人沾光,得到明亮。
因此,我的愿心就是,把佛法的好处、把佛法的智能和智能,分享给全世界的人。这几年来我提倡用「心灵环保」来「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希望世上所有苦难的人,都能分享到佛法慈悲和智能的力量;有的人则是将佛法慈悲和智能的光普照出去。有的人则是被照耀。我不是希望要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佛教徒,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要关怀这个世界,把佛法的好处分享出去,帮助世人减少烦恼,即使是减少一点点也很好。
因此,我这一生走来,虽然多病、虽然艰苦,总是充满感恩。大家知道我的肾功能出了问题,现在必须定期洗肾;我也曾在死亡边缘徘徊,在鬼门关前走了几回,而现在我还能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心愿未了。我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要把法鼓大学建起来。当我的病况一度危急的时候,我向佛菩萨祷告:「如果我的责任已了,没有需要我做的事,那就让我随时走吧,如果佛菩萨还希望我完成任务,那就让我活下来吧。」结果我活下来了,而我的愿望,就是要把法鼓大学建起来。以我目前来讲,死亡或活著并无所谓,但是,活著是佛菩萨给我的责任、给我的使命、给我的任务,我还是要全力以赴地活,活得有精神、有活力。
刚才枢机主教说,死亡以后,就跟天主的大爱在一起,与神接通;而我死亡以后,则是跟三世一切诸佛同一个生命、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国土、同一个世界,那我还有什么好求的?现在的我很渺小,时间很有限,能够帮助的人也不多;而我死了之后,则不仅是在台湾,不仅是在这个地球、宇宙,而是在无限的时空之中。如此一来,什么地方需要我,我就去!什么时间需要我出使命,我就去!在无限的时空之中,有无限的众生需要帮助与度化,只要哪个地方的缘成熟了,我就去!这就是我的因果观。
因果小的,会在小的时空范围里运转,因果大的,则没有时空的观念,没有时空的关系。并不一定是说,我在这个地球上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希望再到地球上来享福报,这不是真正佛法的观念,因为这样的时空范围太小。在无限的时空之中,只有无限大的愿心,以及慈悲和智能的功能,要广度一切众生。
真正的自由
问:最后请教两位大师,您们觉得您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遗憾?或是觉得还没有做,需要更努力去完成的事?另外,全世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都是生荣死哀,两位毕生都主持过许多次丧礼,见证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请问两位要如何安排自己的「最后一程」?希望所有关心您们,爱您们的人如何参于?
师:有人问过我,这一生之中,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如果马上死了,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对我来讲,我曾经犯过无数的错,但这不是遗憾,因为无知,所以犯了错。而我不会再去犯曾经犯过的错,也就没有遗憾了。
至于有没有想要做而还没完成的事?的确是有无数的事想做,却还没做。这些年来,我们每年都会推出一项社会运动,例如,我们率先对于民间大拜拜、大烧香、大烧纸钱或大放鞭炮等习俗提出改革,过去台湾民间常见从一村吃过一村,从这个镇吃到那个镇的大拜拜习俗等情况,现在都已经渐渐减少了。
另外,几年前还推动一项「心五四」运动,就是从「心」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主张。像现在社会上普遍知道的「四它」——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或是「四要」——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能要该要的才要,不能要不该要的绝对不要等等,我们这个团体里有几十万人经常在用,成为日常必需的一种生活方法。
去年,我们推出「心六伦」运动。因为中国古代的「五伦」,在今日社会已经不适用,有些观念显得八股、守旧,新世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大概不容易接受,所以我们透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来推广「心六伦」运动。
今年,我们则倡导「好愿在人间」运动,呼吁大家一起来许好愿、做好事、转好运。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并不是仅仅推动一段时期就够了,而是要持续、普 遍地推广下去。
这个世间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在我的心中,我的愿是无穷的,只要对社会是好的,是社会需要的,我都愿意去做,一项一项的做。若是我个人无法做的,我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在我这一生做不完的,希望再来人间继续推动,继续广邀大众一起参于。所以,我这一生,没有遗憾,但是我的心愿永远是无穷的!
至于死后,我希望与佛菩萨在一起,之后,若是佛菩萨需要我到哪里,我就 去哪里,或许这也是随著我的心愿而去。而我往生以后,别人对我做任何评论,这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刚才枢机主教说,死后不希望有人送花,不希望有人歌功颂德,也不希望舖张、追悼。而在过去,罗光主教往生,我去凭吊时,看到他的棺木停在一个大厅里,其余什么也没有,这是个非常好的示范。但是在佛教界,过去有些例子显得比较舖张,灵堂布置得富丽堂皇,并且举办追思、传供。传供就是集合很多长老法师来供养十道斋菜,然后一道一道地传,可说是身后哀荣了。但是我死后,这些都不要。
我早已预立遗嘱,而且经过律师和法院的公证;我个人没有财产,我的著作归属于教团;我的遗体用薄薄的木板封钉就可以了,火化以后,既不设牌位、不立碑、不建坟,也不需要盖一个骨灰塔来占位置。
法鼓山上有一处「台北县立金山环保生命园区」,是一座植葬公园,这是由法鼓山捐地给台北县政府,再由台北县政府交由法鼓山管理维护。所谓植葬,就是把骨灰分成好几分,分别放入散在公园各处、已经凿好的几个地穴之中,这样就不会让后人执著地认为某块地方是自己眷属或亲人的。
不论任何宗教或民族,只要愿意把骨灰植葬在这个公园里,我们都接受,而且植葬的过程中,也不会有宗教仪式。到公园来的人,不准献花、烧纸、烧香,或是点蜡烛,就只是凭吊。其实人死了以后,就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或许暂时会有人记得,但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人们就忘掉了。过去厚葬的做法并不文明,也不经济,非常浪费,即使你有个很大的坟墓,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还是会被忘记,例如中国的秦始皇等君主,他们的坟墓现在只是变成观光景点,而不是真正去纪念他。
现在,法鼓山上的环保生命园区才开放没多久,已经有几十个往生者植葬了,十年以后,可能会有数千人以上。如果有人来凭吊,那就数千人一起凭吊了。未来,我的骨灰也会植葬在这个公园中,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处,所以我死了以后, 骨灰也可以做为肥料,因为公园四周种了绿竹,将来还可以生产绿竹笋,而骨灰也就变成肥料了。
因此,我的想法跟枢机主教非常类似,希望我们的做法能形成一种风气,也希望日后能够有名人或高僧大德也一起这么做,让我们的社会真正走向一个文明的时代。












 净界法师
净界法师 妙莲老和尚
妙莲老和尚 宏海法师
宏海法师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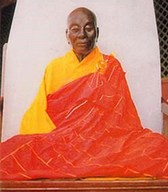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净慧法师
净慧法师 其他法师
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 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