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到话头禅,事实上话头禅并不是一个发明,而是很多唐朝的大祖师们,在非常灵活、随机应变地接引学人的方法中,有一些自己特殊的方便。比如说有的禅师碰到学人过来,不管学人给他提什么问题,他可能都是一个回答,比如说“莫妄想”,就是一个回答。或者不管学人提什么问题,他总是竖一个手指头,天龙俱胝和尚就是那样的。或者是上堂的时候问大众“是什么?”,百丈禅师下堂句,上堂以后下来的时候问大家“是什么?”。
这样的一些特殊方便,对于学人来说就是一个话头的效果,令学人在内心生起疑:哎?师父为什么这么说?师父为什么总是那样问呢?师父举一个手指头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生起疑了。所以说话头禅是宋朝以后比较普遍流行的,是从禅门里早期祖师们接引学人的这些方便中提炼出来的。
参究的话头有很多,昨天我有列举一些。柏林禅寺是赵州祖师的道场,赵州祖师有一个很有名的公案,有人问他“狗子有佛性吗?”他说“无”。当然后面还有对话,但是就到这里为止,他为什么说“无”?这个“无”的回答成为参禅的人参究的话头,这被称为“无字禅”。
宋朝有一位无门慧开禅师,他有一本书叫《无门关》,第一篇就讲赵州和尚的“无”。无门慧开禅师是南宋末年的大和尚,他一生也以提倡参究“无”为入禅的方便法门。在他的语录里,有很多赞叹这个法门的开示,他讲到这个“无”就是一把金刚宝剑。
我们怎么参究它呢?他讲的是八万四千毫窍,三百六十骨节,通身起疑:为什么他说无?对于“无”这个字,在这个字上不能生起分别,把它当成有无的无、落于理路去思维;当成虚无的无,让心去找一种虚无的感觉,停在里面,那也不对。
总而言之,它的要点在于他为什么说“无”,而不能在“无”这个字上生起思维分别。那么我想参“谁”,“念佛的是谁?”,它也是一个字啊,虽然话头不一样,但是它的功用是一样的,这个功用就是要截断我们的妄想分别。
大家不管是参“无”,还是参“谁”,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感觉到无从下手,不得要领,心里不知道往哪儿去想。我想特别是参“无”的时候,这种不知道从哪儿下手的感觉更加明显,更加突出。
为什么?因为参“谁”,你好像还可以找一找,“谁”它究竟在哪儿?念佛的是谁?会不会在心脏里面?会不会在肚子里面?会不会在脑子里面?会不会在身体外面?会不会在身体里面?会不会在身体与外面的中间?你还可能会去搜寻,但是参“无”,上来就是一个让你无从下手的天罗地网,把你笼罩其中。
我想参“谁”的人也会这样,他只要方法对头,他一定会这样,就是怎么下手,找不到感觉。我现在想跟你们讲的是,你感觉无从下手,这就是你下手的地方。你感觉无从下手,就对了,你说你找不到感觉,就对了,你说你心不知道往哪儿想,就对了。
所以参禅其实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为什么?因为无量劫来,多生多劫,不管白天黑夜,我们的心就是习惯于在一个理路上走,在一个有滋味上走,在一个有下手的地方去走,在一个可以想、可以推理的地方去走。但是参话头的要害,就在于把你的路给斩断了,把我们一向以来多生多劫的这个习惯,用这个话头铁壁银山一一拦住。
所以说参,坐在那儿很闷、心胸很烦闷,脑子也不知道想什么,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心没有一个出路,这个对啊!你敢面对这种状态吗?你敢承担这种状态吗?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敢不断地提话头吗?你敢吗?如果你敢,这就是参禅。
如果你还想在话头里面,按照一个理路,按照一个意思,按照一个法义,甚至是你去找一种感觉,找一种说法,找一种理解,那就大错!那就不是参话头。读佛经的时候正思维,思维佛经,如理思维,那个可以的,但是参话头的“参”,不是思维。
“参”这个法门奇特之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掉一向以来我们心里的运作习惯。有一个词叫心路,我们心里的路有好多条,有很多路径。我们一向以来所习惯走的那条路,就是分别、执取的路,在分别这一点上建立很多见解,《楞严经》讲叫立见,站立的立。在执取这一点上,建立有你、有我、有他,有对、有错、有是、有非,让我们轮回的就是这个。
你说:哎呀!找不到感觉,没味道。让我们轮回的就是有味道的东西,就是你认为有感觉的东西,就是你认为有路可走,有理可循的东西,所以参话头参“无”。你参“无”,这个“无”前面讲了,慧开禅师说,它仿佛一把金刚宝剑,它就是要斩断我们过去的这种心路。但是你还不放弃,念念不间断地提起它、提起它。
你之所以能坚持不断地提起它,最初要有一番信心,对这个法门的信心,对祖师的信心。你觉得无路可走,你觉得心里的烦闷被放大了。祖师们开示,参话头的时候心里越烦闷越好,类似于参“无”、参“谁”这样的话头,他们有很多精彩的比喻,说仿佛是拿一个生铁做的桩——生铁橛啊,在嘴里咬。还有一个比喻说,仿佛是吃那个用木头渣子做的汤,就是木工加工木器以后剩下的渣子,你把这个木头渣子煮成汤来,去嚼去吃,有味道吗?没味道。无门慧开禅师说仿佛咬了一个铁球在嘴里。
咬铁橛这个比喻很生动,它比喻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分别心,就如同人的嘴巴里的牙齿,它总是要咬一个东西(我们的分别心念念不休息的,它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咬着,它不咬的话,它受不了),那么现在我们扔给这个分别心嘴巴的是一个生铁做的铁棍,给它咬,它咬不动啊!咬不动,它就不断地咬。促使我们不断地咬的,从根本上讲就是信心。
刚才我们讲到疑情,你为什么能生起疑情?还是因为你有信心,你对祖师有信心,对自心与佛无二有信心,你才能真实疑——有真实的信,才有真实的疑。所以说你就不断地咬,后果是什么?所以这个比喻很生动就在这儿了,它的后果是:我们要是咬铁橛子,可能会把我们满口的牙齿全部咬碎掉。哎呀!很痛啊!比喻在这个话头之下,我们的分别念如同牙齿一样会被粉碎掉。
从教理上看,坐禅有止和观。他说参话头这个方法里面,止观尽在其中,有止也有观。参话头这个方法,不仅仅使我们全力以赴,专注于话头——这就有止,那么我们妄念也逐渐地少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的内心起分别执著的那种习气,被话头给研磨掉了,使这个习气不再活跃。我们的心有很多种路径,无量劫以来最熟悉的那个分别执取的路径,当它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的路径。
大家不要认为只有这一个分别执取的路径。因为现代西方人,他们也研究佛学,也有很多高僧到西方去,所以他们以修行人的脑电波做实验对象,做各种研究。以他们研究的成果来说,事实上,我们人的心脑、心智活动,这种以我执、以自我为基础所建立的推理、分析、判断,就是分别执取这个心路,只是我们心理活动生命中的一面,不是全体。当这一面变得不活跃的时候,那么另外一面会出现。
因此也可以用类似于太极图来描述我们的心智活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就是一种是以自我为基础的这种分析、判断、推理、执著;一种是直观的,直觉的,超越二元对立,对于多数人来说,当一种活动炽盛的时候,另外一种就会变得衰弱。
所以我们把话头当成一个铁棍子不断地咬,没有味道,它的一个后果就是会让我们分别执取的习气慢慢地歇下来。但是讲咬铁橛,意思是说,我们在参话头的时候必须要改变以前用别的方法用功的方向。你心里觉得闷,觉得无路可走,那么这种方法对了。
也许有的人会说,那是不是参话头的人一直就在这种痛苦之中啊?在这种烦闷中啊?恰恰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往往你觉得心里千头万绪,慢慢地尘埃落定,慢慢地只有话头。
只有话头的时候又闷,心又无路可走,又找不到出路,仿佛一条狗被关在一个门窗钉死的房间里,然后房间里有人拿棍子打它,它要四处去逃避,得找一个门往外跑,可是又找不到,所以在最初会烦闷,会觉得无路可走。比如说,这个狗它老是往门那里跑,但是门永远是锁着的,它总跑过去,但是总也跑不出去,最后它就不跑了,也不往门那跑,也不往窗那跑。
在这个过程中,止的受用会出现。止的受用,其实也就是乱念——各种各样的念头,变成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这个话头。
依照我们坐禅的身、心、气统一的规律,在你用功夫的过程中你不断地提:赵州祖师为什么说“无”?或者简单地你想个“无”,但是当你想“无”的时候,要带着疑去想,把你的意念专注在“无”上面。
按照我们身、心、气统一的规律,你的意念老是专注在这个“无”字上,慢慢地这个“无”字仿佛会变成一个外在的对象,比如说它好像在你的胸中(当然我通常提倡,不管是参“无”还是参“谁”,你先不要把它放在胸中,放在鼻端最好),然后把眼睛睁开,看着。但是你们不要误解,观想一个“无”字,观想一个“谁”字,这就错了。
我前面讲了身、心、气有统一性,你老是全力以赴聚焦于“无”的时候,它的那种生动感、直观感,不亚于你身边的禅凳或者衣服。这是你的功夫有进境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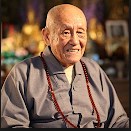 梦参老和尚
梦参老和尚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 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妙莲老和尚
妙莲老和尚 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 其他法师
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